
在陈问村的作品中,文字的元素反复出现在不同艺术媒介的各个角落。这些字词往往是零散而架空的,以“掠影”(Glimpses)的形式驻留在观者的视线中,仿佛在飞驰的汽车上不断经过路边的标语,由文本落在视网膜的瞬间留下强烈却含混的片段性印象。“语言”被拆解成由单个字词构成的基本组分,继而被重组,形成新的艺术表达的语言体系。艺术家借助文字这一会使人“不受控地去理解”的元素,以强势的姿态占领性地传递给观者的艺术内涵。

对艺术家而言,创作是他“诉说”的方式。有时候文字仿佛谜语,帮助他在具象化的、追求“意义”的现实世界通过抽象和模糊创造可供休憩或探索的空隙,获得抽离的表达空间。在尝试的过程中,陈问村逐渐构筑起自己的艺术语言体系。他将打散的片段性字词通过这个体系整合,试图使其成为“make sense”的完整景观。其中一半是带有与生俱来的意义的字词,另一半则是绘画、影像等不同形态的艺术语言。

然而,“make sense”也并不是艺术家所追求的标准答案。进一步拆解这一短语,“sense”不仅仅可以指代“道理”和“意义”,也可以代表“感官”,而这正是艺术家所追求的:用艺术的语言造句时,“理解”就不仅仅局限于对文字的阅读理解,而是一种多感官的交互,联动意识与直觉的共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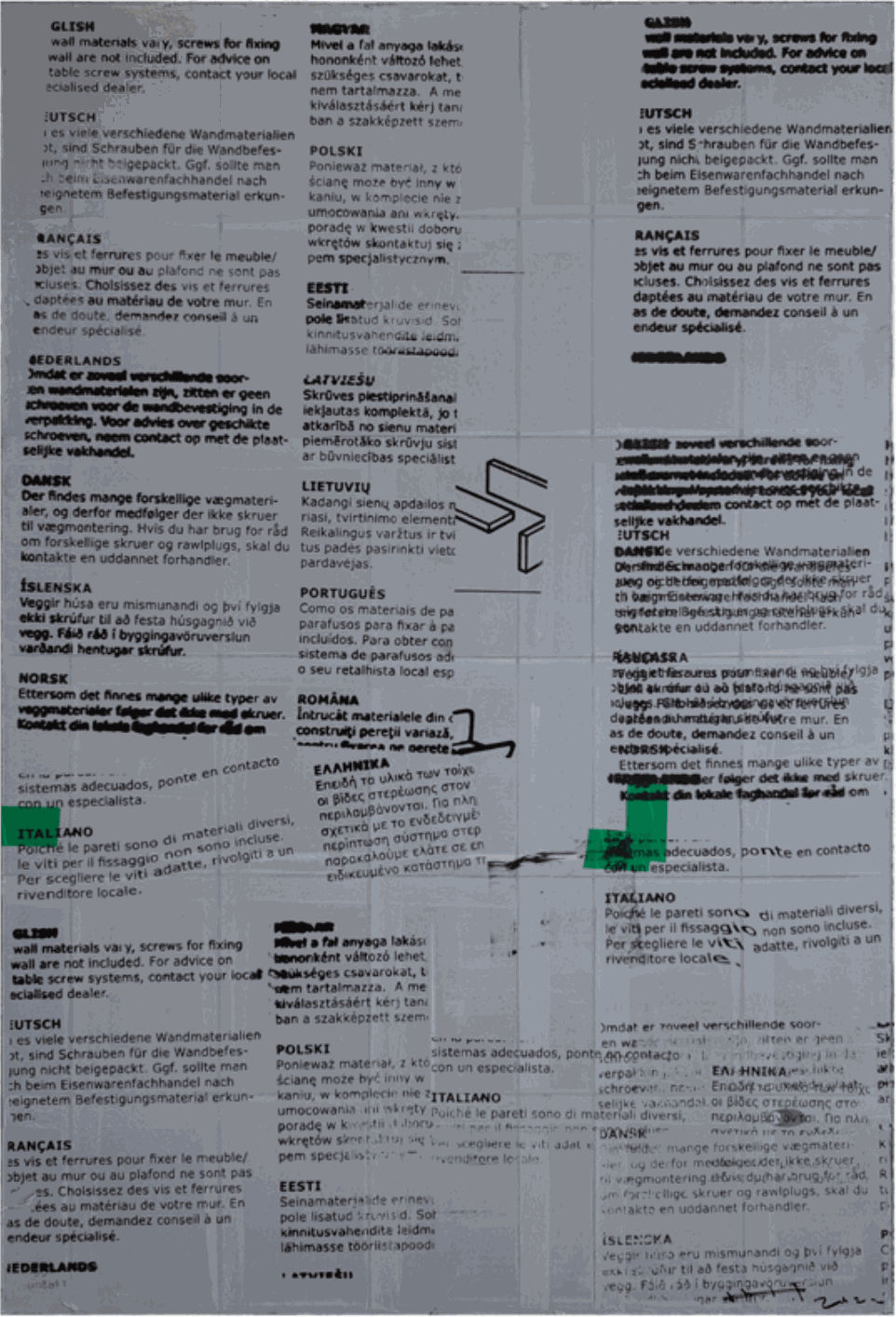
像组成语言的字符一样,艺术家始终关注如同分子一样构建物质的“基本单位”。在早期作品《比尔 布雷克斯》(Bill Bricks)中,艺术家在油纸上印制了未经切割的半透明纸币图样,并使用来自破裂旧仓库门的木板封印在墙面上。重复的纸币作为基本单位,仿佛重复诉说的词句,令人联想到《闪灵》中著名的‘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’的重复书写,一种压抑下的僵化行为和其中暗涌的、即将爆发的宣泄。人对于财富的渴望在作品中被具象化,而其对精神的影响或摧残也借由语言体系变得显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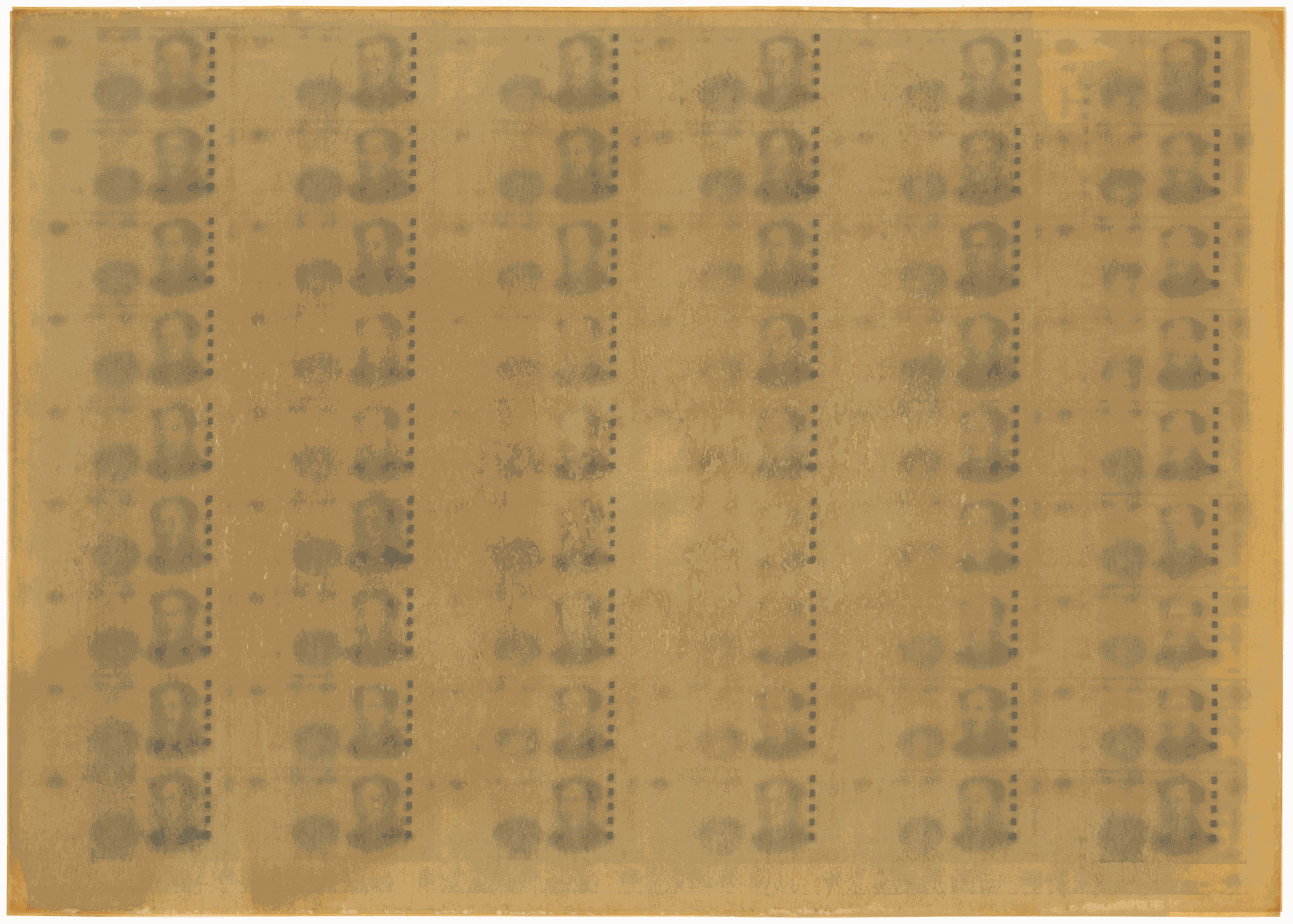
在其后的创作中,艺术家对于组装的兴趣一直延续,而表现形式也从简单的重复扩展到了不同零件的组装,这似乎呼应了艺术家语言体系和用语能力的扩张。在作品《运作》(How to get a work done)中,陈问村借用了宜家(Ikea)这一经典品牌和其代表的蓝色,并延用了宜家家具需要自己组装的核心特征。整体的物件被拆解成功能分明的零件,并被赋予了近似管理学概念中的流程功能,将社会体系中的程序变得如同组装家具一样可视。作品企图展现的完整信息也如同句子般,由零件的画作单词组成拼接,徐徐展开,如对话般向观者传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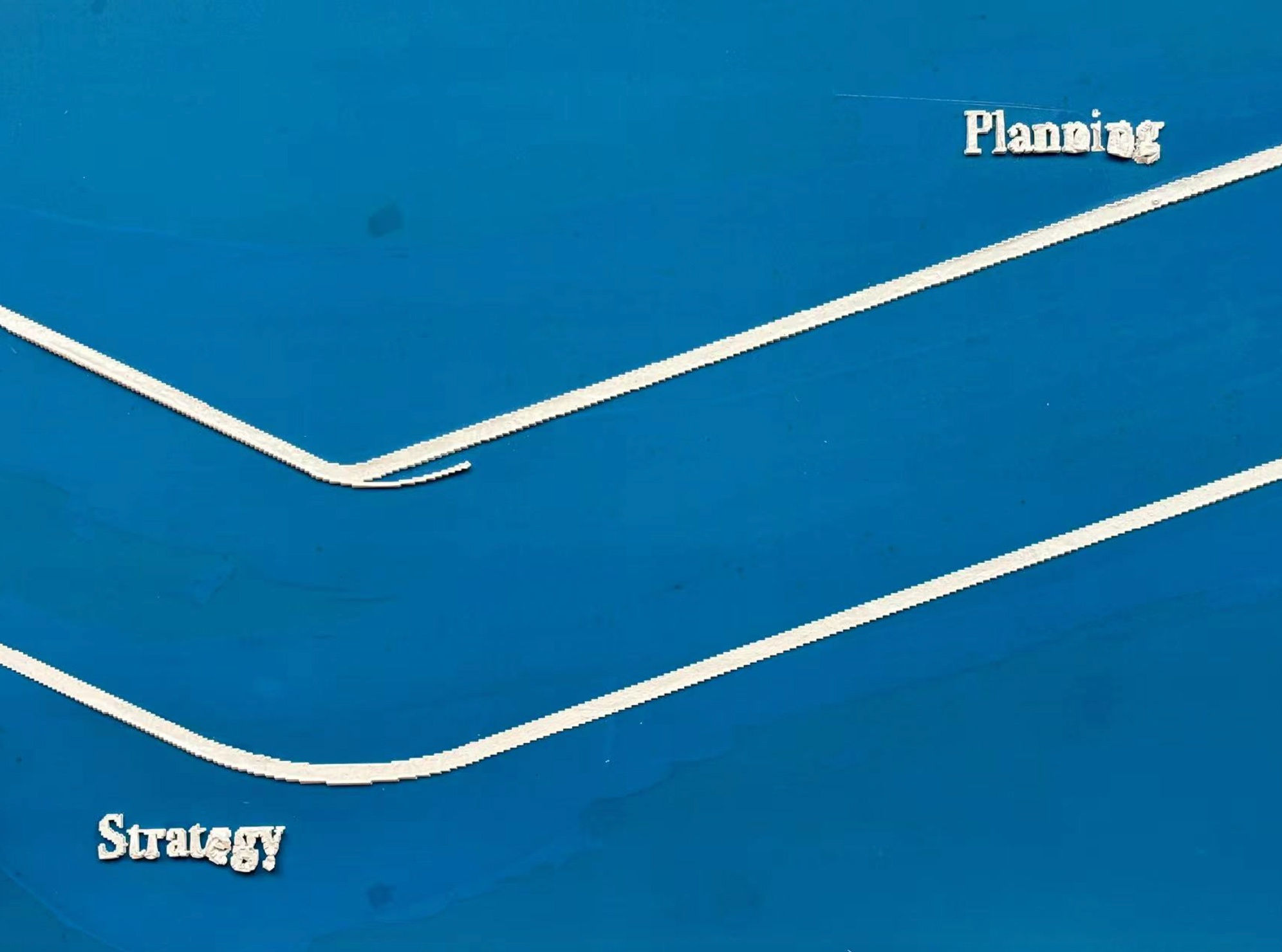
陈问村作品 《运作》(How to get a work done) 局部照片,图片由艺术家提供。
对陈问村而言,大学老师的身份使他在创作中一直保持着学习、进展的蓬勃状态。在他看来,这个时代中的我们处于一个充满可能性的“过程”里。新的技术、艺术语言不断涌现,填补着纯语言的空白,也给艺术家以更自如地表达的机会。
维特根斯坦“语言游戏学”的理论主张语言是在游戏般的交互中习得的。语言在使用中被每个使用者赋予了各自所理解的意义,而并没有“本质主义”的绝对意义。对于陈问村而言,创造自己的艺术语言系统也是如此。它在艺术实践中更新、扩张并迭代,而每一件艺术品的产生也就如同“造句”,重点在于创造的过程。在艺术创作中,不断地学习和充盈自己的语言库,将作品像饱含信息的语句一样创造出来,与观者交流并聆听回声。

在展览《造句》中,语言和艺术表达是同源的,都具备创造交流的力量和生机。这种力量建构在字、词和短句的基础之上,又由创造性的艺术表达所补全。陈问村的作品不断叩问着二维的边界,以对话般的精神力量寻求多维性的、感官的体验和回应。在这里,粗糙或精炼,含混或直白,都成为了仿佛语言学习一般的螺旋上升过程,吸引人走进,对话;或者阅读,旁观。
文/付若瑄


